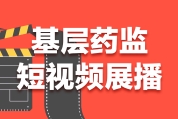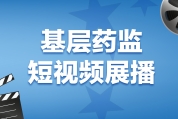中成药高价治理:是压成本还是挤水分
- 2025-09-05 16:13
- 作者:刘雨蒙
-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网
中国食品药品网讯 有关部门对中成药价格“亮剑”还在继续:8月26日,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发布通知,要求不同厂牌间价差较大的中成药进行价格申报;9月1日,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公示,将8月21日价格虚高治理行动中涉及的中成药价格处理结果对外公布。
自7月以来,十余个省份陆续开展中成药挂网价风险处置行动,拉清单、比差价,敦促与省份内同品类最低价差价较大的中成药产品限期降价。与密集的价格治理行动一并引起关注的,是在清单中同一品种悬殊的价格。在各地公布的价格治理清单中,部分中成药挂网价与省份内同品种最低价显现出20倍、100倍,甚至900倍价差。
中成药挂网价差为何如此悬殊?本次价格治理行动会对涉及风险处置的中成药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专家向记者表示,高倍差价中存在一定“水分”,价格风险处置工作有利于挤出虚高价格,但也给部分中成药企业带来挑战。
“价差10倍,暂停挂网”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小活络丸申报价格高于省同品种最低价915倍;广东百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牛黄解毒片申报价格是省内同品种最低价的456倍;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柴胡注射液的申报价格是省内同品种最低价的126倍……这是黑龙江省药械集采平台8月22日公布的一份中成药价格风险治理通知中显现出的价格差异。
记者看到,黑龙江省对于处置清单中的245款中成药,均折算成日用价,与省内同品类最低价相比,其中价差少则3倍,多则915倍。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进行价格治理的地区。
吉林省7月22日及8月21日分别公布了两批中成药价格虚高治理清单,共计111款产品,有37个产品在省内最低价的20倍以上,其中价差最大的达到117倍。
内蒙古自治区7月18日和8月21日相继公布了213种存在价格风险的中成药产品,其中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血塞通注射液日用价格是省内同品种日用最低价的162倍;河南泰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复方丹参片日用价达85.5元,而省内同品种日用最低价仅有0.55元。
对于高价产品,黑龙江省要求,如果在调价后仍与省内日用最低价差在3至5倍以内将被划为黄标管理,5至10倍则将纳入红标管理,10倍以上则暂停挂网。
绝大多数省份与黑龙江省类似,以高于省内最低价3倍、5倍为节点,设置“红标”或“黄标”,对价格进行分级分类风险处置。按照各地的价格风险处置要求,高价产品应在限期内主动调价,逾期未调整或调整不达标的,将面临暂停挂网处理。
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朱明峰表示,被纳入“红标”或“黄标”管理范畴的中成药,或将在医疗机构采购时以弹窗形式进行高价风险提示,这会对产品的采购量产生影响,他认为,大部分公立医疗机构不会选择采购价格风险产品。
价差差的是什么
不同企业的同名中成药为何存在价差?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存在价差是合理的,但如果价差过大,则值得商榷。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指出,原料品质与生产工艺的差异是中成药价格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生产生脉饮时,企业若选用红参,其成本远高于党参,其成药市场价格自然不同。”此外,同一品种不同剂型工艺也会影响定价,如相对于胶囊剂,软胶囊、滴丸等因制备流程复杂、原料成本较高,价格也随之上升。
山东某中成药企业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即便为同名同方药,仅“含糖”与“不含糖”,其成药在工艺成本及辅料价格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也会造成同品规中成药之间的“价差”。“如果在公开的价格治理清单中,将某一品种的含糖产品和无糖产品放在一起,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大价差。”
然而价格悬殊并不一定合理。
在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刘张林看来,越是大规模、规范化生产的企业,越有可能因大量销售补齐成本,将市场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同企业同一品种的生产成本差别通常在百分之几十,按常理来说,其市场价格出现一倍以上差距的可能性极低。”刘张林表示。
邓勇也表示,当前数据中呈现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差价存在“水分”。在他看来,部分药企以高标准为由高定价,但其实际质量是否能与高价匹配,很难判断。
另外,也有专家猜测,当前同一品种存在的价差可能与部分企业恶意压低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有关。“例如某些参与挂网的产品已临近有效期,企业便大幅降价处理。”刘张林说。
企业各有选择
毫无疑问,面对多地集采平台发出的价格风险预警,中成药企业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降还是不降?
记者采访获悉,不同企业基于自身产品结构、成本控制和市场策略,对于接到的价格风险预警,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我们企业暂不考虑调价。”朱明峰表示,为保产品质量,企业未来可能将考虑退出本轮申请的中成药继续参与挂网。
据悉,由于地方在执行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结果时遵循省际价格联动机制,企业对于调价极为谨慎。今年上半年,湖北、山西、江苏等省份发布的“执行全国中成药联盟集中采购中选结果”相关通知中均明确,如在执行期内出现新的省际中选价或挂网价低于中选价格的,企业应在新价执行后一段时间内主动调整价格。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人士也向记者透露:“我们宁愿放弃部分区域市场,也不轻易下调价格,因为一省降价可能引发全国价格联动,影响整体运营。”
但也有企业趋向于主动下调价格,保证产品市场份额。
吉林某中成药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将通过压缩用工成本、参与集采“以量换价”争取微薄利润。
9月1日,吉林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也公布了第二批中成药价格虚高产品价格调整结果,共有17家企业降价。其中,一款关节止痛膏价格下调了38.3元;一款小儿咽扁颗粒从45元下调至42.7元;一款香砂养胃丸则由98元调整为32.4元。
在中成药价格治理中,也有企业担心,持续压低价格会对中成药企业,尤其对执行高标准、用料工艺优的企业造成冲击。不仅如此,同品名的低价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还将影响消费者对中成药整体的信任。
但有专家指出,敦促差价较大的中成药降价并非单一方向的施压,也将引导行业走向良性竞争。“对于那些成本控制能力强、产品质量过硬、注重研发创新的企业,本轮治理实为发展机遇。”邓勇表示。(刘雨蒙)
《中国医药报》社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责任编辑:宋莉)
分享至
右键点击另存二维码!
-
相关阅读
-
为你推荐